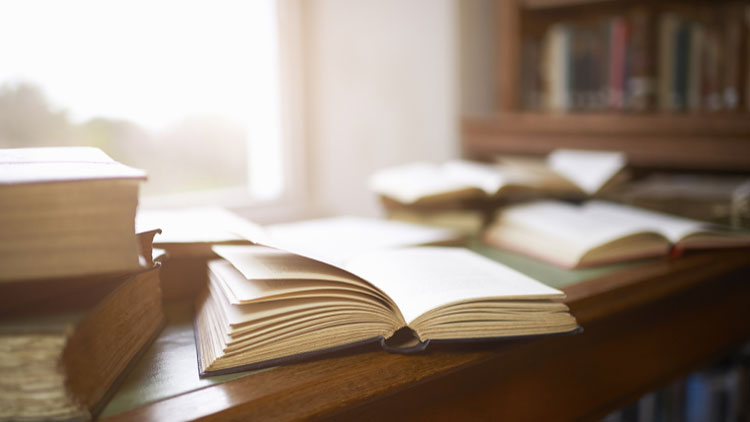金庸作品中的“景语皆情语”
发布时间 :2021-12-03按西方关于小说的理论来看,小说的三大要素是:环境、人物、情节。金庸先生曾说:“小说是写给人看的,小说的内容是人。”人物的品行由情节反映,人物和情节是小说的主体。环境往往作为小说的修饰。虽然环境不是小说的主体,但是,没有环境描写的小说,读起来是味同嚼蜡的。
在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里,文字间多穿插环境描写,读来犹如身临其境,直击人心。

一、暗示背景
小说开篇的环境描写,多以渲染气氛为主,感情表述上如果是破败、残旧的,往往你就能预料到接下来的情节不会太愉快。比如《射雕英雄传》整篇开头:
钱塘江浩浩江水,日日夜夜无穷无休的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,东流入海。江畔一排数十株乌柏树,叶子似火烧般红,正是八月天时。村前村后的野草刚起始变黄,一抹斜阳映照之下,更增了几分萧索。
开篇寥寥数语,就让人感受到萧索之意,江水日日夜夜流去,“奔流到海不复回”。有如英雄末路,又似乎在诉说南宋统治岌岌可危,大厦将倾,一下子就定下了悲哀和无奈的感情基调。果不其然,而后描写郭杨二人,一个名将之后、一个梁山好汉后代,一身武艺,却背井离乡,屈居于小村落里耕田度日,令人惋惜。
最后郭杨两家人的结局也是十分悲惨,生离死别,颠沛流离,仿佛一开始的悲凉感就注定了悲惨的结局。
读金庸先生的作品,你会发现还有很多这样的描写,环境描写,暗示情节的悲喜,营造了一种无法逃脱的宿命感。
二、人物塑造
这种营造氛围的写法在人物塑造方面也有体现。同样是“风雪惊变”中,丘处机踏雪而来,全身白雪也不损其威风,将一位傲立于风雪的侠客风姿描写得淋漓尽致:
忽听得东边大路上传来一阵踏雪之声,脚步起落极快,三人转头望去,却见是个道士。那道士头戴斗笠,身披蓑衣,全身罩满了白雪,背上斜插一柄长剑,剑把上黄色丝条在风中左右飞扬,风雪满天,大步独行,实在气概非凡。
这是不是和现在推崇的“氛围感自拍”有异曲同工之妙呢?

不止自然景物,人也是一种特别的景,由人构成的场景下,着重描写一人的出场,更能显示出其重要性:
眼见攻来的兵马又要支持不住,忽然数十支号角齐声吹动,一阵急鼓,进攻的军士大声欢呼:“铁木真大汗来啦,大汗来啦!”双方军士手不停斗,却不住转头向东方张望……只见黄沙蔽天之中,一队人马急驰而来,队中高高举起一根长杆,杆上挂着几丛白毛。欢呼声由远而近,进攻的兵马勇气百倍,先到的兵马阵脚登时散乱……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汉子纵马上了土山。他头戴铁盔,下颏生了一丛褐色胡子,双目一转,精光四射。
在战场上以威猛之势出场,双方军士皆侧目,铁木真仿佛战神降临,势不可挡。
三、交代情节、烘托感情
王国维曾言:“有景语,情语之别,不知一切景语,皆情语也。”虽是描写客观的景物,但以人的主观言语加以表达,景色描写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个人情感的抒发。
古往今来,人用大自然抒发情感的例子比比皆是,在《小石潭记》中,
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,隔篁竹,闻水声,如鸣珮环,心乐之…… 以其境过清,不可久居,乃记之而去。
被贬官后的柳宗元开始有游玩之兴致,一想到自身经历后逐渐伤感,对小石潭经历了由喜到悲的感情变化。
在《书剑恩仇录》中,陆菲青遭遇追杀后反杀三人:
荒山上寒风凛冽,一勾残月从云中现出,照见横尸在乱石上的三具尸首,远林中夜枭怪声凄叫,他虽然艺高胆大,不禁也感惊心……
他为了躲避仇家追杀,多年来躲到陕西总兵李可秀府中,这次为保性命再次出手,瞬息间又重新回到腥风血雨的江湖斗争,一时心惊也是情有可原。

在推动情节发展时,往往会穿插景物描写,固然可以理解为是在交代之后的情节场景,那请你再看看这段:
众人仰望山峰,此时近观,更觉惊心动魄,心想即在夏日,亦难爬上,眼前满峰是雪,若是冒险攀援,十成中倒有九成要跌个粉身碎骨。只听一阵山风过去,吹得松树枝叶相撞,有似秋潮夜至。
在《雪山飞狐》中,天龙门和陶氏父子等人迫于宝树大师威势,被“邀请”到山上,心里本来就七上八下,加上这山峰险峻,兼之树影绰绰,更是草木皆兵、风声鹤唳,一下子就把紧张的气氛推到了最高点。
如果只是简单地描写众人被带到一个险峻的山下,心里害怕,反而不能达到这么好的效果,就像现在读到这一段,仿佛还能看到隐匿于云间的皑皑白雪,听到沙沙作响的松林,吹着冰冷的山风,两股战战。
用现在的话来说,金庸先生在情节设置上,真的很会“拿捏人心”。
用景暗喻背景、烘托人物,以景语表情语。从这几个小细节可见,金庸先生以其恰如其当的环境描写,塑造了活灵活现的江湖人物,为我们徐徐展开多姿多彩的武侠世界。